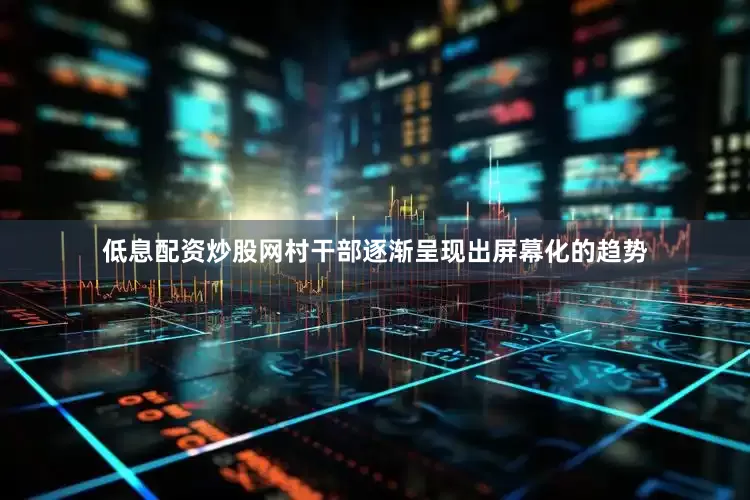

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村干部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中间者”。国家政务平台下乡往往需要村干部对接执行。基于对湘西州政务“平台下乡”过程及村干部平台使用的实践经验研究,本研究发现:村干部需“承包”国家的信息收集、平台下载等数字任务,村干部出现屏幕化趋势。平台界面结构固定了村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身份,国家标准化的数字类型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乡村社会的清晰治理。国家与村干部的互动本质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国家通过平台与村干部互动形成更为制度化的乡村社会交往秩序,这是国家平台的“中间”治理。但平台下乡过程中也出现乡村社会“数字形式主义”“数字悬浮”等问题。本研究旨在对村干部平台使用的经验进行研究或创新数字时代国家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
向青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0&ZD320)、“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项目编号:GZB20240840)的阶段性成果。

2020年10月,研究员在观察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村级微信群的过程中,注意到村干部发布了“湘医保APP”下载与操作方法。在微信群中,村干部号召村民学习数字平台的安装注册,并将其安装的截图发给村干部。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湘西州试图自上而下地推动数字政务平台、数字治理小程序等进入社会治理系统的末端——村庄。自上而下的“数字下乡”首先要经过村干部,村干部是国家数字平台的使用者。一直以来,政治学、社会学领域不乏对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过程、村干部权威等的研究(贺雪峰,1999;王铭铭,王斯福,1997;郑卫东,2013),但较少研究关注村干部的平台使用。传播的信息与信息处理技术共同生成控制革命(Beniger,1986:6-24)。数字时代,国家通过规范化、制度化及指标化的技术手段进行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王雨磊,2017)。技术形塑着互动的制度与模式,应观察技术和社会治理行动者间的关系、连接、组织及互动,探索技术制度环境变化下行动者行为、权力及结构秩序之间的变化。国家进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国家与代理人的互动既关系着乡村社会的组织化、国家化等问题,也关系到国家认同、国家政权合法性及国家治理有效性。基于以上,本研究初步提出研究问题:国家如何通过数字平台与村干部互动?国家数字“平台下乡”如何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一
文献综述
(一)乡村治理中国家-村干部关系的相关研究
在科层组织结构形态中,中国政府的委托代理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层层委托代理(江依妮,曾明,2010)。中央与基层社会需要互动的中介、中间节点以实现和维系治理信息系统的运行。就国家与农民间的关系而言,国家更侧重于对乡村社会乡绅、村干部等“中间层”的治理(周飞舟,2006)。秦晖(2003:2)提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他认为县级以下依靠乡绅以实现自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等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中介。改革开放后,国家与村干部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委托—代理”关系(周勇,1997)。乡村社会治理中,国家需要通过作为“中介”“中间人”的村干部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如图1所示。在漫长的纵向科层组织链条中,“村干部”作为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延伸治理的末端,需要辅助国家以获取乡村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等,并将国家政策等自上而下地传递给村民。如在精准扶贫任务中,帮扶单位也要借助村委的权威、社会网络关系及社会治理信息等完成扶贫任务(王雨磊,2017)。也就是说,在国家—村干部—乡村社会的互动模式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家与村干部的委托—代理关系。

但所有的“委托—代理”关系均存在信息不平等、信息差等问题。这其中滋生出代理人道德风险、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ary power)的风险(张维迎,1996)。乡村社会治理中也存在“委托—代理”的假设冲突(刘有贵,蒋年云,2006)。一是国家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国家委托人与代理人村干部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村干部是赢利特征明显的个人(狄金华,钟涨宝,2014)。由于委托人监督难度较大,村干部可能会利用专断控制、高度垄断信息等方式,实现侵占这类集体资产的机会主义行为(王钰文,王茂福,2022)。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非正式制度的动态性、模糊性及不对等等问题(张晓晶,2012)。如贺雪峰(2011)认为,在农业税时期,乡村社会“内卷化”(involution)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二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作为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的村干部(张龙,2020),其能与村民直接互动,但却与决策者存在相对距离(Masood & Nisar,2022)。这导致“委托人并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努力工作程度”(刘有贵,蒋年云,2006:70)。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着中间代理人俘获国家资源、村民冷漠治理、村干部监控不足等社会治理乱象(李祖佩,2017)。国家需将中间代理人纳入更为制度化、规范化的组织结构。进一步而言,国家治理系统中对政治系统“中介”的治理及其权力调整意味着国家对乡村社会非正式权力的规范。
(二)媒介逻辑下平台治理的相关研究
媒介影响着人类的交流、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等,其往往被把握、被建构为“社会秩序”(库尔德利,2012/2014)。媒介逻辑是“特定媒介甚至特定媒介类型形成自身具体属性和做事方式的必然规则”(转引自查德威克,2013/2021:19)。媒介技术治理是国家权力实践的重要表现,现代国家越来越有技术装置的特征(吕德文,2019)。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分别通过“文字下乡”(张建晓,2022)、“广播下乡”(潘祥辉,2019)、“电视下乡”(费爱华,2012)等将社会整合于国家中。数字技术是第三次媒介变革时代的象征,其改变着国家的媒介治理方式、逻辑及结构。国家通过数字平台、小程序等各种数字技术进入乡村社会,形成了国家的“数字下乡”(吴理财,李佳莹,2023)。2010年以后,随着政府部门开发政务平台,诸多研究者对国家平台治理、平台科层结构进行研究(Cordella & Paletti,2019; O’Reilly,2010;Janssen,Charalabidis & Zuiderwijk,2012);与传播相关的“媒介”必须被适当的主体化,甚至建制化(唐士哲,2014)。近年来,我国传播学学者也关注到了平台的协作式治理机制及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李辉,张志安,2021;姬德强,朱泓宇,2021)。
国内外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层面研究国家治理中的数字平台。一是平台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渠道(刘海明,郭珂静,蒋可心,2024;Klievink,Bharosa & Tan,2016;Lee & Kwak,2012;杜超,赵雪娇,2018)。平台的本质是一种协作性极强的组织策略和政社互动渠道。在传统的政府科层体系中,公众表达诉求、村干部信息反馈、国家信息吸纳等均依托于具体的行政部门。数字平台可实现重建政府与社会互动的方式,直接联结供给方(政府)与需求方(公众)的目标(Janowski,Estevez & Baguma,2018)。二是平台对中间代理人“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和强化控制(Faraj,Pachidi & Sayegh,2018)。平台逐渐演化成一种新的组织控制形式,隐含着“治理”和“控制”要素,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Tiwana,Konsynski & Bush,2010)。在数字治理过程层面,中央政府强化了社会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下级政府在公众需求回应上的自主行动能力可能会被压缩(宋锴业,2020)。梳理文献发现,较少研究从乡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的微观视角研究乡村社会的平台治理。当具有“行政机制”“科层”特性的数字政务平台进入乡村社会,其首先与国家代理人村干部产生互动。因此,有必要从村干部的平台使用角度探索数字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变革。基于以上,本研究试图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国家数字下乡过程中,村干部如何使用政务平台?从村干部平台使用的经验而言,数字政务平台可能产生怎样的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二
研究设计
(一)“过程-事件分析”方法
中国是单一制(unitary system)国家。研究某一地域的国家“平台下乡”及村干部数字平台使用并不会削弱本研究的典型性。“很多看似完全不同的事件或行为,背后具有相似的行为逻辑”(张静,2018:128)。在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可采取“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对事物发展的社会过程进行连贯描述和解释,展示事件和过程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孙立平,2000)。村干部平台使用的视角为研究国家政务“平台下乡”和政务平台乡村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了一个切口。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村干部平台使用过程中的“小事件”分析以透视乡村社会治理变化。这其中所渗透的相似行动逻辑或能回答研究员关于国家“平台下乡”的社会治理逻辑。本研究共经历了三个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研究员长期在湘西州进行田野调查。此阶段,研究员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研究了X县村级微信群中的政民沟通过程。观察过程中注意到村干部在村级微信群、朋友圈推广政务平台,遂关注到X县政务“平台下乡”的过程及其问题。
第二阶段:2021年2月到3月。此阶段,研究员为完成博士论文开始深入X县县级融媒体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参与式观察,进入到了X县的乡镇、乡村,了解到基层社会数字形式主义等问题。此后2022年7月到8月,研究员参观考察了H村办公电脑等装置,深入了解了村干部使用手机应用进行数字任务执行过程及数字形式主义等问题。
第三阶段:2023年6月到8月。此阶段,研究员再次进入乡村社会,对村干部如何做好群众工作、与群众进行互动交往进行了访谈,正式开启了村干部媒介使用研究的访谈。
(二)研究材料来源
本研究田野分析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三方面。1.二手资料:主要为地方政府官方网站的资料和新闻报道,村干部微信朋友圈分享内容,村级微信群中有关数字平台下载的信息等。2.文件材料:研究员从乡镇部门获取了数字乡村社会治理相关资料,包括政府手册、组织结构图、对外宣传等。3.访谈材料:研究员与乡镇、村干部通过面对面、电话及微信语音等方式获取访谈材料;为阐述数字平台中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互动问题,本文构建了多层级行动者框架。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如表1所示,具体如下。
(1)村干部。2020年后,湘西州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本文将“一肩挑”的村支书、村主任统称为“村干部”。研究员首先接触到乡镇科员TK,TK为研究员高中同学且在E村驻村。在TK的介绍下,研究员认识了E村村干部GXA。随后研究员采取滚雪球式的方式接触到其他村干部。访谈过程中,TKX告诉研究员,其他村干部的经验类似,研究员即停止扩大访谈对象范围 。根据深度饱和原则最后筛选了17位村干部。需说明的是,访谈对象都直接或间接使用过数字政务平台,不同年龄层村干部使用的频率不同。
(2)行政人员。为能更宏观、更全面地了解村干部数字平台的使用情况,本研究也访谈了X县县委组织部行政人员,其主要工作职责是向村干部传达政策、对村干部进行数字技能培训等。需说明的是,本研究对村干部及C1的访谈主要集中在2023年6月到8月之间;对C2到C5的访谈则在2023年至2024年间陆续完成。本研究共计22位访谈对象,所记录文字约为6.2万字。在效度检验上,研究员后续又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其他15位村干部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结果与本研究结论存在一致性。

三
数字任务的“承包”:
村干部的屏幕化趋势
数字时代的媒介治理逻辑可以不再建立在具体的人、物、事的实际互动之上,而是借助脱嵌于具体时空情境的数字技术使得国家治理能跨越空间距离。数字时代,国家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自上而下地层层进行数字任务的“发包”。村干部则需“承包”下载政务平台、上传数字信息、填写表格等数字任务。湘西州村干部所使用的政务平台及村干部任务执行方式如表2所示。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中介,村干部需具体执行上级行政部门的数字任务。就X县村干部所下载安装的政务平台而言,其中涉及宣传、公安、人社、大数据局及国务院扶贫办等诸多部门。在具体的乡村治理事务中,妇联、民生、公安等每个行政部门都认为其部门的工作重要,诸多数字任务自上而下经过乡镇层层落到村干部(C1、C4、C5等)。如乡镇科员PS(C2,2023年6月8日)在访谈的过程中提到:“一个乡镇需要对接100多个部门,不同的部门都有一些数字任务”。在以数字任务为考核指标的政治锦标赛(political tournament)中,村干部逐渐呈现出屏幕化的趋势。


(一)跨越“空间”:科层末端乡村社会治理信息的收集
传播学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951/2003)认为媒介可分为时间偏向媒介(time-binding media)与空间偏向媒介(space-binding media)。通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行政力量进一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安东尼·吉登斯,1985/1998:214)。治理任务的完成涉及治理者对被治理主体信息的掌握。地方行政部门通过数字平台跨越时空限制将村干部纳入到更具体的乡村社会治理工作系统中,村干部需要完成涉及被代理人数字信息收集任务。处于科层制信息生产链的最末端,村干部承担着乡村社会“最后一公里”原始数据的生产及上传等工作。访谈中,村干部、乡镇干部等(A3、A7、C6等)需要将村庄中的人口、土地、贫困、就业及经历等信息,以数据化、类型化的方式上传至政务平台上,如“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可实现贫困信息的收集等。村干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收集信息:一是村干部一般在村级微信群中发布公告,村民再将所需相关材料拍照传送至村干部,村干部整理后在政务平台上直接上传;在X县,村干部每年都要就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现代公共服务事项“做好老百姓工作”;二是针对媒介素养低的村民或者相关信息模糊、需要实地勘查的状况,村干部则要入户实地获取信息后再上传到平台系统。如2022年夏季,X县要进行“厕所革命”,但由于大量村民在外务工,致使乡村社会“空心化”“老人化”,村干部需要通过入户、电话、微信等方式一家一户地联系村民,再将相关信息数据传输到数字平台上;再如村民住宅信息、土地边界、河流状况等信息都需要村干部现场拍照、勘察获取。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可能有不一样的数字政务平台及相应数字任务等。
(二)数字绩效追逐:平台数字基础设施的注册安装
平台可以理解为政治舞台或表现行为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Plantin et al.,2018;姬德强,2021;孙萍,邱林川,于海青,2021)。数字治理进程中,平台成为国家进行乡村社会治理的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通常而言,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任务极大可能伴随“政务平台下乡”。无论是村庄中社保、医保费用缴纳,还是村路、田地、河流、人口、禁毒、反诈、征兵等各项社会治理事务,只要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推动相关社会治理任务,很大可能伴随着“数字任务”的下乡。如湘西州乡村社会中存在着不戴头盔、无证驾驶、超载等交通安全隐患,县级行政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交通运输局等存在维护交通安全的工作压力(A2、A6、A10)。由此,在X县县级交通部门对乡村“机动车”进行运动式治理过程中,湘西州开发使用“道交安APP”以收集农村驾驶人及机动车等信息;县域交通部门则通过“道交安APP”跨越空间距离对交通安全隐患进行不定期检查。图2为“道交安APP”平台界面结构,村干部需上传农村机动车、农村驾驶人、农村道路等信息。

为推动乡村社会的数字化、平台化,地方行政部门要求村民下载、安装、注册数字政务平台。政务平台的转发和下载成为村干部绩效评估的重要维度,具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性。行政体制内的数字任务落到地方,市县则根据下载量、使用率及使用情况等进行排名。按照州农业农村局、乡镇行政人员(C2、C4、C5、A6)的说法,县级工作微信群要对乡镇平台下载量进行排名,乡镇进一步将具体的任务及压力传导到村干部。因此,为完成数字平台推广、下载及注册等任务,访谈中的诸多村干部反映其被要求加入数十个微信群。村干部被卷入平台下载、图片上传、点赞等“数字绩效”的追逐中。如X县J村人口数量为800多人,村干部需要完成与人口比例相对应的政务平台下载。乡镇干部ZH(C4,2024年7月12日)感受到了数字任务具体执行的压力:“有点儿像湖南超女的模式放在了体系内。我记得有的部门不得不搞,那就不得不买数据了。”数字任务精准到村干部个人,每个村干部则需完成一定数额的平台下载量、注册量等,有的村干部甚至亲自到农民家中“抢手机”下载平台。2022年2月,州、县及乡镇部门一层层下达“智慧湘西”政务平台的注册下载任务(C3、C4、A9等)。仅一个月,2022年3月“智慧湘西”政务平台注册用户已突破10万,累计服务超40万人次(吉首警事,2022)。2022年6月,H村村干部(A8)手机应用上政务平台下载就已达15种。
四
交往的“界面化”:
国家制度化秩序的平台供给
国家与村干部的不同媒介互动逻辑形成了不同的乡村社会秩序,如表3所示。传统媒体时代,国家与村干部的互动主要通过口头、电话、面对面、会议、材料等方式实现。村干部在非制度化、人格化的互动过程中,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国家与村民的需求具有自由裁量权。此过程中,国家委托—代理过程中可能出现信息差、利益偏向等问题,其在村庄中的非标准化政策执行包括资源截取、政策扩大化或缩小执行等。国家则要采取对村干部的监控体制、激励体制以规范村干部的自由裁量权。每个平台都是由多元主体所组成的交往型构(communicative figuration)(刘泱育,2022)。基于数字平台的互动被认为是“中介化交往”(mediated communication)的形态,是个体与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在交互界面的相遇。对于村干部而言,对比传统媒体时代行政与人情复合的互动治理,数字时代国家通过政务平台与村干部互动,其所形成的是国家非人格化、制度化的交互形态。

(一)平台界面结构:村干部国家代理人身份的固定
湘西州PS曾为驻村干部,具有乡镇、驻村等基层工作经历。他认为过去在农业税征收、计划生育等政策的执行上,村干部非标准化政策执行导致村民产生不公正感、不平衡感,这进而造成乡村社会干群关系的恶化。村干部具有国家、公共及私人混合属性,村干部身份的“公私转换”或产生牟利等行为(杜姣,2023)。过去,村干部安全检查随意性很强、对国家政策的学习也往往以自发为主。从媒介逻辑而言,政务平台具有规则、制度、次序等结构特征(李净净,马良灿,2023),实现了对科层组织关系、结构、行动的再造,将村干部原本自由、分散、碎片化、日常化的工作纳入到国家平台制度规则范围内。村干部的屏幕化行为具有公共性、非人格性等特征,其根据国家平台设定的规则将村务信息上传,村干部的社会治理行为被纳入到平台制度结构中。如上级行政部门通过政务平台要求村干部清理河道、网格巡视、耕地情况、住宅基地等。此外,政务平台的“数字留痕”(digital footprint)对村干部社会治理行为进行了具体约束。如在“打卡签到”“拍照证明”“在线学习”“实地打卡”等“数字留痕”的过程中(A2、A8、A11等),村干部被纳入到平台制度所产生的治理结构中,其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身份及其具体治理行为等被固定下来。如“湖南省林长制管理系统”强制规定了村干部的巡视时间、路线及次数等。村干部YDH(A3,2023年7月3日)认为:“对比以前工作,有了数字化后,工作比起原来有更大的留痕,能让乡镇和村民时时都见到,对(村务)治理的公开化、公众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数字乡村治理趋势下,部分国家数字平台逐渐普及,甚至可跨越村干部直接与年轻村民、在外务工村民互动,这减少了作为互动“中间人”村干部的信息扭曲行为。乡镇干部ZH(C4,2024年7月12日)告诉研究员:“过去,村民和村干部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在办理各项服务的时候。村民找村干部盖个章可能还需要给村干部递包烟。”大量基于村干部人格的非正式治理行为影响了村民的公平感、被剥夺感及是非观等。平台成为双边和多边社会连接和关系的“中介”(intermediary)。国家“平台下乡”后,村民与村干部的诸多交往事项转化为村民与政务平台、村干部与政务平台惯例化、标准化及制度化的数字交往方式。技术嵌入官僚制度,在国家与乡村社会接点上衍生出全新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权力分配格局。在国家自上而下部分资源流动分配过程中,村干部不再实际参与资源分配。政务平台所形成的媒介治理逻辑强化了对村干部的约束和规范,防范代理人可能存在的资源截取行为、实现对村干部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平台运作模式下,国家与村民、村干部的交往方式、交往内容及交往效果等得到规范。如访谈中村干部普遍认为缴纳农村医疗合作的费用几乎透明,村民自己就可以上缴医保。村民能在政务平台查阅费用缴纳信息,村干部很难再如农业税时期利用信息差隐瞒社保、医保等信息。如村干部HTL(A7,2022年6月6日)认为:“乡村治理数字化方便了村民办事,例如下载‘智慧人社’后,村民可以自行在该APP上进行养老认证,不用亲自到村部办理。”
(二)形成数字类型:平台的清晰化治理
L村村干部TY大学毕业后进入村组织,相对于村中的其他村干部,他擅长采用如数字文档收集具体的、分类的社会治理信息。他(A12,2022年6月19日)认为:“以前村里农合收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还易出错,更难对相关资料进行归档。现在数字化后,我们可以直接缴纳社保、医保,信息不会出错。”
从政务平台与村干部的交互内容而言,其主要通过将繁杂的乡村社会日常事务类型化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从村干部的平台使用经验而言,政务平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乡村社会治理事务进行分类。一是乡村社会治理内容的分类。数字平台可实现对教育、医疗、交通、住宅等不同内容类型的治理。通过国家政务平台,村干部将乡村社会诸多复杂的日常生活问题进行类型化处理。不同政务平台所能实现的交互内容、交互治理效能等并不相同,村干部需在不同类型平台间进行切换。如村干部普遍需要登录“学习强国”学习领导人讲话、法律政策等进行积分排名。2022年湖南长沙自建房倒塌事件后,村干部需在“全国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湖南省)”上传本村自建房、危房等相关信息。二是乡村社会公共服务流程的分类。数字技术将政府组织体系内各个部门及具有同类功能的社会治理主体均纳入到政务平台“桌面”,通过数字技术以实现标准化的、流程化的乡村社会治理。乡镇行政人员需将流程任务信息等分发到村干部,村干部则使用电脑或手机做成数字表格,再通过政务平台上传本村的医保、道路等信息。村干部基于政务平台的具体规则要求上传国家所需要的乡村社会信息。此层面而言,政务平台提高了乡村社会治理类型规则供给的适配性。
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1939/1991:215)在《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中提出日常生活世界以“类型化”(typification)的方式而存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建立在分类工作上。如卢曼(Luhmann)将社会系统分为机器、有机体、心理系统及社会系统(约阿斯,克诺伯,2004/2021:247)。街头官僚往往基于“组织规则、分类体系和运作程序的‘内部世界’与社会信息和需求的‘外部世界’”互动(Prottas,1978:292)。村干部处于国家组织规则与乡村社会互动的“中间地带”。更具体地说,村干部需同时具有适应行政规则及对乡村社会事务进行分类的双重能力。传统媒体时代,村干部与国家的互动具象化为与县级、乡镇行政人员的互动。行政人员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知识专家拥有对国家政策的阐释权,但村干部的政策理解能力、工作能力及负责态度等参差不齐。如面临村内数百户的医保缴纳信息,村干部往往凭借记忆和笔记本等进行记录;一旦工作繁忙或者稍不仔细,就会出现农村农合收缴出错、信息上报失误等问题(A7、A2、A11、C4)。政务平台将世界置入日常事务中,提供了服务互动内容编码信息的手段,其本质是将社会治理事务符号化、类型化。平台内容与流程的类型化将乡村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模式进行重复,并形成了简约化、类型化的社会治理数据。对于原本处于模糊治理状态的村干部而言(A1、A4、A9等),数字平台让其能更准确掌握国家所需收集信息。
“为使国家官员能掌握现实总体的方方面面,必须将复杂的现实简化为纲要的条目”(斯科特,1998/2019:102)。斯科特(1998/2019)认为,现代国家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借助清晰化的测量工具,实施一种简约和标准的度量政治学(politics of measurement)。平台数据化指的是以人为核心的交往实践被转化为可计量、可分析的数据。依托于数字技术,国家的数字化治理可实现对社会治理对象及其行为实体的虚拟化、数据化等。“在这种意义上,数据涉及某种形式的物质化(通过媒介及其基础设施),进而带来特定的知识制度化” (库尔德利,赫普,2017/2023:156)。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被纳入到数字政务平台的标准流程,村干部的社会治理行为可留存、跟踪及测量。如湘西州诸多村庄的身份证办理、医疗报销、社会报销等事务均可在政务平台上实现。按照米歇尔·福柯(2007/2009:286) 对治理的思考,治理技术可将社会变成可理解的图解。国家治理的前提正是将社会变成一整套“清晰化图解”(schema of intelligibility),但分类及其子过程充满建构性和权力意味(方文,2017)。国家是平台符号权力的重要来源、规制者及执行者。对于国家而言,乡村社会平台治理中的内容及流程类型成为类型化的清晰图解,国家可以清晰地实现对乡村社会治理内容的“可视”(visible)。在收集村庄医保、住宅状况、林地及人口信息等过程中,乡镇、村干部能通过界面全面了解村中医保缴纳名单、贫困家庭具体情况等。如80后村干部YDH在村中工作了8年,他(A3,2022年7月3日)认为:“村务能以数字表格等方式保存、反复查阅。”
(三)平台秩序供给:国家技术理性“嵌入”与村干部的“数字抗拒”
韦伯(1978)认为,中国传统的帝国治理主要依赖儒士熟练运用儒学经典,而以税务管理为代表的计量技术则粗放、落后。黄仁宇指出:即便到了明朝,帝国统治者依然以道德整合国家与社会,而没有发展出基于理性的数目字管理。他指出:“中国下层各种经济因素尚未造成一种可以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情势……最下层的数字既不能复实,中上层之经理亦受影响,所谓各种黑暗与腐败,并非全系道德问题,而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技术问题存在。”黄仁宇(2006:29-30)认为近代中国失败的根源在于以道德代替技术进行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需解决技术治理的问题。乡村社会形成了基于血缘与地缘的“差序格局”社会。因居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中介”“结点”互动的位置,村干部拥有信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流动的权力。但基于地方权力文化网络(power culture network)的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常采取“搞关系”“潜规则”和“走后门”等非正式互动方式,使得社会公平性也受到侵蚀(周雪光,2017)。复杂社会治理中,基于村干部人格的治理并不稳固。村干部在自由裁量权下具有一定的谋私行为等,此问题导致基层干部权威的普遍化下降。乡村社会治理中,国家面临着规范及约束村干部谋私所滋生的特殊主义、关系主义等问题。
每个交互界面意义的每一次变动都需要对其所协调的社会关系和空间类型进行再次定义(盖恩,比尔,2008/2015:51-52)。在传统媒体时代,国家与村干部间的面对面、文字交往等形成了人情与行政复合的乡村社会治理秩序。平台型治理(platform-based governance)被称为与科层治理等治理范式并列的“第四种治理模式”(Janssena & Estevez,2013)。政务平台是科层组织内部制度结构和生产模式的变革。国家通过技术建构微观互动情境,将原本非正式的、漂浮的、可公私流动的乡村社会治理事务固定下来,以平台制度结构限定或引导互动的主体、内容及模式等。“媒介”是生产、传播和接收内容的“制度化”形式和平台(库尔德利,2012/2014:1)。韦伯所提到的“数目字管理”本质是数字技术治理问题。此“数字技术”恰如韦伯(2005/2010:46)所提出的科层制中的“就事论事”,按照特定的规则流程以实施社会治理。数字平台成为国家乡村社会治理的数字基础设施,形成了基于平台“界面”的乡村社会互动治理模式,具有去村干部中间互动中介——个人化(personalization)、人格化(humanization)等特性,以实现国家与村干部间界面化、制度化的互动,如图3所示。

但数字平台融合转型的“行政机制”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内部场域产生了冲突性的复杂治理情境。一方面,数字平台所产生的“标准化”治理形成了“一刀切”的问题。村干部FGM在本村脱贫致富、河道改造等上政绩显著,但他抗拒数字任务的执行,他(A10,2022年6月6日)认为:“很多APP会搞很多任务,很多任务都是虚的、空的、形式的、编的。上面很多学识派,坐在办公室想的东西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们想的和老百姓的切身感受还是有出入的。”村干部所认为的数字任务“虚空”等问题(A8、A10、A15)本质上是数字技术数据、类型等平台规则难以适应乡村社会复杂的实际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数字平台本身出现的功能欠缺、系统卡顿等问题,也缺乏相应线下配套措施。尽管国家自上而下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和成本推广、安装服务型数字平台,但村干部往往在安装后便不再使用。此外,尽管国家通过数字平台、数字系统进入乡村社会,但却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以实现数据获取,村干部也只能无奈配合。如在乡村危房状况的具体数据收集中,村干部认为其并不是专业的安全评估人员,难以作为危房信息数据员(A3、A5、A10)。此外,在村干部具体信息收集的过程中,存在大量无法避免的人为的和客观的数据失真情况(C4、C5、C6等)。部分村干部更关心“数字任务”的完成(A1、A7、A12),而不是数字准确、数据真实等。如果时间紧张,村干部甚至通过“统计加估计”或“外包购买数字服务”等方式进行数字抵抗。由此,数字政务平台仍“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在乡镇干部TKX(2023年8月20日)看来:“上面的规定很奇葩。但很多任务布置下来,就像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不好的作业,(任务)布置错了,学生也不敢说什么,只能模模糊糊照做。”
五
研究总结与反思:
国家平台的“中间”治理与国家能力
乡村社会治理常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如若保护基层政权威信,往往激化基层政权和社会的利益冲突;如果保护村民权益,又不能不在结果上“损害”基层政权的权力,国家政策执行缺乏代理人权威以进行具体的社会治理(张静,1999)。代理人作为“中间沟通机构和非正式制度”关系到国家公共服务供给与政治稳定(Tsai,2017)。历来,国家对“中间”的治理与调整都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建设(孔飞力,2002/2013:24)。国家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如何通过不同媒介技术促进信息交流、减少委托者与代理人间的信息差距、规范村干部自由裁量权等重要问题,以促进国家与村干部交互的制度化、理性化。平台本质上是国家对信息技术与科层技术的双重使用,更是国家治理组织及其相应治理效能优化的重要媒介方式。基于对村干部平台媒介使用的研究,本研究发现:数字乡村治理趋势下,国家与村干部的“委托—代理”关系或转换为数字任务的“发包”与“承包”。国家以政务服务平台为“交互界面”形成国家与村干部交往形式的再变革。与传统“国家—村干部”互动模式不同的是,村干部在界面平台上与国家的互动产生标准化、非人格化的社会治理特性,形成国家的“界面化治理”(interface based governance)。在平台乡村社会治理事务类型供给的过程中,国家所实现的是乡村社会清晰化、标准化治理,以形成对国家治理系统末端——村干部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与约束。国家技术理性或逐渐替代灰色的、模糊的、变动的中间层的非正式地方治理。这是数字时代国家平台的“中间治理”(the governance of intermediation)。
“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伊尼斯(1951/2003:40)如此评价媒介所产生的国家治理功能。政治学家曼(1993)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政治权力——专断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他认为,国家要通过完善自上而下的信息交流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国家的基础权力(Mann,1984)。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文字作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极大地扩展了国家的交往空间。国家、代理人及村民的传统互动治理模式下,一旦社区单位组织中的乡绅、村干部等互动中介脱离国家,则意味着乡村社会偏离于国家,地方的非正式组织力量由此影响乡村社会秩序。从国家乡村社会媒介治理逻辑而言,数字平台是国家深入乡村社会的数字基础设施。国家基于政务平台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交往是国家权力建构、国家主导的技术主义路线。数字治理趋势下,国家通过平台将村干部纳入组织结构系统中,以平台的交往秩序规范约束村干部的行为,其本质是将乡村社会纳入到新型交往结构中。在国家数字平台治理转向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交往逐渐“界面化”,乡村社会被直接纳入到国家技术治理范围,“中间”沟通者——村干部的自主性削弱。在未来国家数字治理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交互出现更为制度化、理性化的转向。此层面而言,数字时代国家平台治理能力也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下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国家与社会交往互动的生动实践。数字下乡过程中,国家平台的标准化也面临着地方差异特性及乡村社会复杂治理等问题,这其中是社会治理行动者冲突、博弈及合作复杂过程。本研究以村干部平台使用的经验作为切口或能为数字时代国家与乡村社会交往互动与乡村社会治理等提供新视角。当下及未来都是观察和研究国家数字下乡过程的重要阶段。未来,研究者或可就“平台下乡”过程研究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过程、行动者权力互动及博弈过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行动者的权力边界及村干部媒介素养及数字形式主义等问题。
本文参考文献、注释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3期。
本期执编/许鑫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mall.11185.cn/h5/#/bkGoodsDetails?spuId=113613&from=imgShare&dsId=zxSWChat&dsModule=c3df4964-af5d-40a8-d6cc-a768b5306e52 ,进入中国邮政微商城订阅本刊。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
进入官网下载原文

西宁股票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